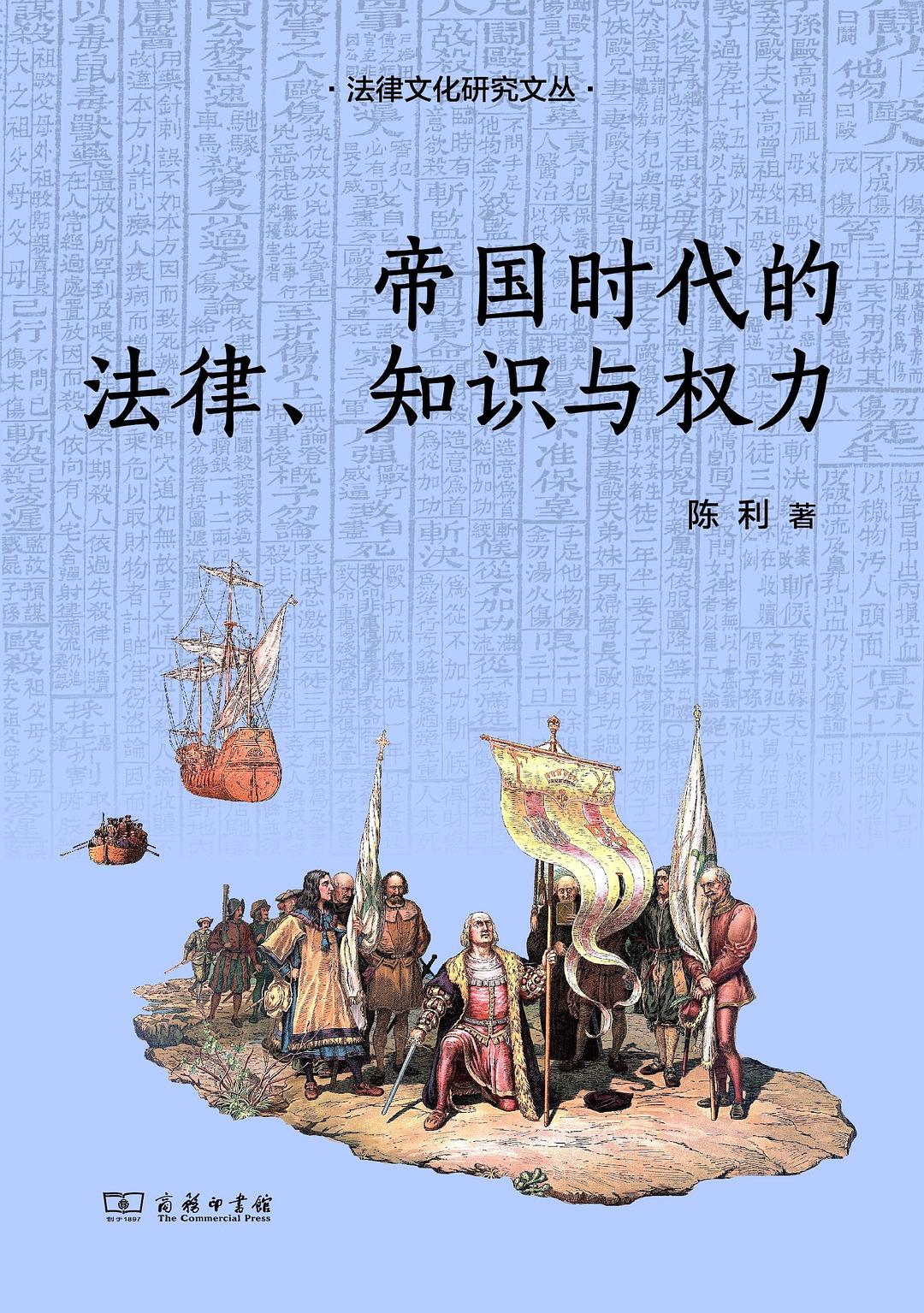
《帝国时代的法律、知识与权力》,[加]陈利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11月,575页,98.00元
华裔历史学家、多伦多大学陈利教授近期出版的文集《帝国时代的法律、知识与权力》收录了作者自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二十余年间有关中国法律史、比较法律史等领域的十四篇代表性论文、札记和访谈,展现了帝国研究的视野与法律史这一学术领域相遇时的火花。本书表明,近代以来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历史,在中西法律史上划下了深深的痕迹。即使在今日,对帝国的法律遗产展开剖析乃至清算,也仍然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的研究风格
在出版这部中文文集之前,陈利的英文专著《帝国眼中的中国法:主权、正义与跨文化政治》(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已于2016年问世,并荣获2018年亚洲研究协会(AAS)最佳著作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Prize)。该著的翻译工作正在进展中,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也会与中文读者见面。在某种意义上,《帝国时代的法律、知识与权力》这本文集是对前一著作的补充和完善。不过本文集中相当数量的论文也越出了《帝国眼中的中国法》的原有论域(但也并不是毫无关联),而且预示着一本新的大部头专著正在形成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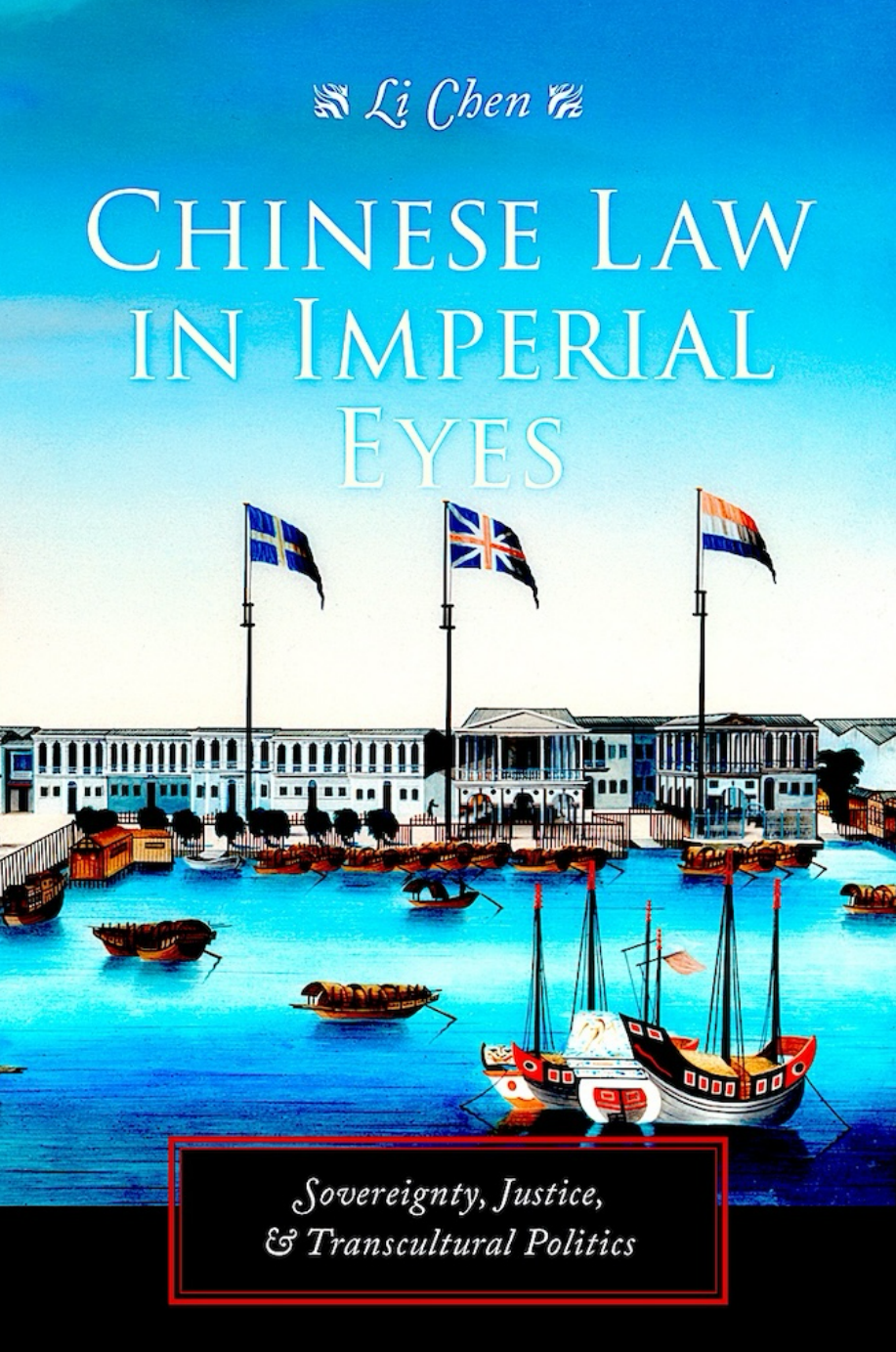
陈利2016年英文专著《帝国眼中的中国法:主权、正义与跨文化政治》
由于是文集,本书不存在如专著那般严格的问题意识、论证结构和最终结论。但在我看来,很明显有一种突出的视野或“风格”贯穿全书几乎所有文章,亦即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的研究风格。学术流派意义上的后殖民主义,是一种批判性理论框架或思维方式,它既关注殖民统治时期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围绕这种权力关系产生出的身份建构、文化霸权等现象,又揭示和清算正式殖民统治结束后的种种殖民遗产。对中国读者来说,最为著名的后殖民主义学者莫过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其《东方主义》(Orientalism,又译《东方学》)一书借助深刻的话语分析方法,揭示出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乃至文化界是如何刻画出一个方方面面都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彻底“他者”般的东方形象,以及这种刻板造型是如何服务于西方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目的的(参见[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在中国法学界,一度声名大噪的络德睦(Teemu Ruskola)的《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也对顽固存在于近现代西方法律界有关“中国无法律/法治”的话语展开批判性的分析,因此可算是后殖民主义法律史学的重要作品(参见[美]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魏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在后殖民主义批判性思维的指引下,《帝国时代的法律、知识与权力》第一编处理了近代中西互动背景下的诸多法律史和国际法议题。在第一章中,作者引领我们重温了1784年发生于广州港的“休斯夫人号”(Lady Hughes)案件。该案中一名英国水手随意鸣放礼炮导致两名中国人死亡,在中方坚持下,嫌犯最终被中方审判并处决。本案长期以来被西方视为“中国法律野蛮、落后”的证据,而这一野蛮性话语也构成后来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制度的一个正当性依据。借助对中西方档案等资料的详细梳理,本章颠覆了“中方将意外事件作为杀人案来处理”“中方固执于一命抵一命,中国法律不区分故意和过失”“同时期英国法律比中国法更‘现代’”等一系列陈旧说法,并指出西方坚持确立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原因,并非真的在于“中国法律野蛮”,而毋宁是出于帝国的傲慢以及更“安全”地(或者说更无所顾忌地)在中国攫取诸种利益的目的。第二章质疑了西方近代国际法理论上的平等主权神话,并指出国际法学自其诞生以来,就始终坚持西方基督教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和人民享有种种特权,包括将自己主权拓展到非西方地区的权利。第三章讨论了近代情感帝国主义及其对中国的适用:当某些侵略行为实在无法在严格的、技术性的国际法层面获得辩论时,政客和商人们就诉诸西方人的情感受到中方某些行为(如没收鸦片这一“英国人的财产”)的伤害这一理由,希望以此煽动议会和公众的愤怒乃至仇恨情绪。第四章揭示了近代列强为确保自身安全和利益而在中国实施“绝对责任”政策:一旦在中国某地发生伤害缔约国官民的行为(如教案),那么涉事地区的民众就要承担集体连带责任,而地方官乃至督抚也必须受到清廷的处分乃至刑罚。第五章讨论了近代以来乃至当代国际“伤害索赔”中的“有趣”现象:强者声称自己受到弱者伤害,并立刻以战争的形式实施报复,同时长期掩盖弱者受到的来自强者的更大伤害。
从表面上,本书第二编是对清朝“内部”法律史的探讨,并没有明显呈现出近代中西互动或后殖民的视野。但本编在某种程度上仍是后殖民主义研究思路的延续,或至少是对后殖民史学的重要补充:在对西方近代以来建构的“中国法律野蛮”话语本身展开充分解构之后,一名真诚的历史学家有必要去回答,前近代中国法律究竟为何。对帝制中国法(尤其是作为晚期帝制法的清代法)本身展开扎实的经验研究,揭示其丰富、多维的意涵及其与近现代社会的对接潜力,同样能够有力回击种种有关中国法野蛮、落后的殖民话语。陈利在此处的研究重心是清代法律职业群体,尤其是“司法幕友”这一群体(陈利创造“司法幕友”一词,而不是使用刑名幕友这一常见称谓,是因为钱谷幕友在实践中也深度参与州县司法活动)。本编对清代司法幕友的形成与成熟、幕友律学著作(幕学)、法律职业群体结构和规模、皇权对幕友的管控及其局限等议题均有探讨。在清代法律职业群体的规模上,陈利指出,清代讼师规模长期维持在至少“1700至2000名”,刑部有品级司官人数约为一百至三百人(时间越靠后人数越多),司法幕友则长期维持在三千余人(330页,337-338页,352页)。如果是计算清朝数百年间所产生的法律职业人员的总量,那么可以认为“在1700年至1900年的两个世纪里,清朝大约有六千至九千名受过培训的司法官员、一万七千至两万名有一定法律知识的讼师,以及至少三万到六万名受过系统法律培训的司法幕友”(355页)。本编最后一章讨论的是晚清法律以来中国法律人的“自我东方主义”现象,亦即主动将中国法视为一种“传统法”,并将其置于作为“现代法”之西方法的对立面的做法(更详细的讨论参见下文)。
在本书第三编中,陈利结合自己的求学和教研经历,向读者分享了其在法律史教学和研究方面的一些认识。此编讨论了如何以跨学科的方法辨别和解读史料、瞿同祖著作的价值和可能局限、对包括法律史学在内的历史学课程应如何展开教学等问题。相信这些内容也一定能对相关读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和博士研究生)产生重要启发。此编中让我尤其感到“欣慰”和共鸣的是,作者表示北美大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普遍衰退,“这里也包括英语是母语的学生”(482页)。我本人在国内的教学经历也让我在这方面深有感触。因此这可能是互联网和信息化时代的全球“通病”,值得严肃思考与对待。
几个突出的亮点:平等主权神话、认知暴力与经典反思
本书几乎各章内容都是亮点,其视野之敏锐、洞见之深刻、史料之扎实,均值得称道。上文已提及的第一编中对“休斯夫人号”案件及相关话语的颠覆性研究,以及近代列强对华的情感帝国主义实践,相信均能对读者造成足够冲击,并激发学术讨论。限于篇幅,在此仅就我在本次阅读中感受到对我个人而言具有极强刺激和共鸣的某些内容和观点,予以介绍和讨论。
本书第二章质疑的是近代国际法的平等主权神话,在讨论中涉及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的主权之争。学术界对该事件常规解释框架早已为我们所熟悉:自居于天朝上国、固步自封的清朝拒绝与西方国家展开平等交往和贸易。尽管学界已有更具反思性的作品,使我们对清廷在对外交往方面的考量,以及清廷在对外关系中采取的礼仪制度,有着更深入、更同情式的理解(参见[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但陈利作品所揭示的英方在此过程中的狂妄态度仍旧让我震撼。英王乔治三世国书官方译本(即使它已被添入一些外交上的委婉表达)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呈现出了英方在军事上自吹自擂乃至近乎威胁态度:
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平安。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并不是要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也不是为贪图买卖便宜;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处,各处事情物件,可以彼此通融……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此时,不但大西洋都平安,就是小西洋红毛邻国的人他没有理同本国打仗,也都平复了。如今,本国于各处全平安了……(转引自本书111-112页)
我实在是看不出来这些文字如何体现出近代国际法的“平等主权”和“相互尊重”精神。相反,乾隆帝对英王的回复倒是更体现出捍卫国际法上领土主权的意味:“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海岛、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转引自本书115页)。这一来一回实在让人疑惑,究竟谁才是骄傲自大,谁才是尊重主权平等?
本书第十章“中国法的传统化:晚清法律改革背后的国际话语政治和认知暴力”展现的是近代中西法律交流史上的一种“象征性认知暴力”现象:晚清知识分子和法律人是如何在西方话语的刺激下,逐步将本国法律理解成一种与现代法律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传统法”的。这种本国法的传统化在清末礼法之争中达到高峰。一方面,这种“自我东方主义”话语既被代表“进步”力量的法理派所利用,以服务于其尽速仿行西法改良法制、撤废领事裁判权和促进社会变革的目的。另一方面,作为“保守”一方的礼教派实际上也受到法律东方主义话语的影响,从而将中国法理解成拥有固定本质的、与西方法格格不入的事物。换言之,法理派和保守派实际上共享着法律东方主义的认识论,亦即都认为中国法是西方近代法的绝对他者,他们的差异仅在于对这种遭到他者化的中国法的价值评判(一方认为应该抛弃不适合现代性的中国法,一方则视之为应予保留的国粹)。而且正如陈利所言,虽然曾经作为法理派干将的汪荣宝、董康等人在民国时期曾质疑过自己在礼法之争中的观点,但是这些反思“仍然透露出文化帝国主义在认知方面的象征暴力和后果,因为他们仍在使用自我东方化的话语,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和法律传统及社会历史的复杂现实,高度浓缩为那似乎一成不变的纲常礼教、家族主义和社会秩序”(424页)。这种所谓的反思与批判看似是对西方的抵抗,但由于其深层的认识论仍是东方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认识论,所以其实际结果很可能是巩固了西方的认知霸权,并且“经常抹杀了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历史复杂性以及可能具有的共性或可比性”(426页)。
使用东方主义画笔描绘的中国法形象,导致大量本应继承、值得继承的中国本土法律元素在法律近代化运动中被瞬间抛弃,更导致(延续至今的)百余年学术史和文化史上中国法的那种公式化、本质化的理解,进而阻碍学者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全面和深入理解。中华法律文化不是只有皇权专制、卡迪司法/情理法交融或个案中的衡平(这几种说法在根本意义上其实是一回事,无非是价值评判上存在差别)、礼教纲常或家族主义。中国法还有家产官僚制下司法体系(尤其是中央司法制度)的职业主义倾向,还有大一统理想与实践作用下愈加明显的社会身份齐平化趋势,还有宋代以来的土地私有化运动及随之产生的高度复杂的财产习惯,还有晚期帝制集权式简约治理下对民间社会经济生活原则上的放任态度以及对私有产权的明确保护趋势……建基于西方霸权的有关中国法的象征性认知暴力在近代对中国法的伤害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因为我们无法穿越回历史中去改变本土法律的近代命运。然而,至少我们当代学者可以做到也有义务做到对这种认知暴力保持时刻警惕,尽可能去反思那种确曾盛行一时的有关中西法文化的本质主义的、过度僵硬的类型学认识(这里绝对没有否定类型学之价值的意思),尽可能避免东方主义遗产对中国法律文化的二次伤害。
本书第十二章是对中国法律史学奠基人之一瞿同祖先生两部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清代地方政府》——的反思。此处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对前一部作品及其中“法律儒家化”命题的讨论(我本人的相关看法,参见赖骏楠、景风华:《法律儒家化未曾发生?——以家庭法制为中心》,《学术月刊》2023年第2期)。在充分尊重瞿老学术贡献的基础上,陈利指出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在理论框架上可能存在的一个局限:一种“整体主义”视角导致瞿老认为帝制中国社会结构在近两千年时间中未发生本质变化,因而与此种社会需求相配套的法律也未曾发生重大变化。这实际上是十八、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中国停滞论”的二十世纪社会科学表达。这种停滞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二战后全球学术所扬弃,但陈利书中的反思性文字在我看来仍值得引用:
但是,这种将复杂和动态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实践活动,极度简化成一个似乎可以超越时空变化的定性概括,往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面临各种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这种文化本质主义所产生的宏大叙事或论断所依据的理论框架本身,不仅倾向于回避现存史料的人为构建性(constructedness)和残缺性(partiality),还经常企图超越或无视人类历史所具有的偶发性(contingency)、流动性(fluidity)和内部矛盾或不稳定性(intemal conflictuality/instability)。(457页)
更有意思的是,陈利也在本章中介绍了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英文版(1961)问世后西方学术界以书评等形式对该作品的反馈。实际上包括杜希德(Denis Twitchett)、范德沃克(van der Valk)、斐利民(Maurice Freedom)和包恒(David Buxbaum)等学者在内的海外汉学界都曾对瞿著中的“中国停滞论”倾向表达过批评意见(457-461页)。很可惜这些声音长期以来并未能在国内学界引起反响。对各人文社会科学的近现代学术史展开全面、系统的梳理,剖析其中经典作品因时代因素导致的认识局限,提炼出这些作品中仍值得发扬光大的认识和洞见,并以当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概念进一步发展这些有益洞见,或许是当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事业中的一个关键任务。
进一步的思考
本书若干面向也刺激我产生若干进一步的思考,这或许意味着某些有意义的研究思路。例如,第一章提到,在“休斯夫人号”案件后,西方长期主张中国对命案的处理态度是简单粗暴的“一命抵一命”方式,并以此作为确立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借口。这种话语无疑是对自唐代以来就拥有复杂精致之“七杀”罪名体系的中国法的污蔑。但本书也显示,甚至连乾隆帝本人的上谕中就出现了“抵拟”这样的字眼(59页)。我本人阅读晚清律学家薛允升《读例存疑》时,也在其对部分涉及命案的律、例的讨论中,体会到一种较为明显的“命抵”逻辑。原本只是用来处理械斗案这种极端情形的命抵原则,何以被拓展到其他命案中,是否可能发生该原则的滥用,该原则的适用对传统“七杀”体系构成何种冲击等问题,或许对清代法律史研究本身而言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当然,这里绝对没有为殖民话语“开脱”的意图,毕竟在涉外命案中,中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既没有意愿、又没有能力实施命抵原则。
又如,对于领事裁判权对中国造成了何种具体伤害问题,作者似乎倾向于解释为列强通过该制度包庇和纵容本国人的在华暴力犯罪行为。但考虑到这些列强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势力拓展到中国也主要是为了攫取经济利益,那么领事裁判权对其在华工商业利益的额外照顾也就值得当代学者展开细致研究。我们尤其需要关注领事裁判权日常实践中的大量民商事案件(杀人放火案件的数量自然远远少于商业纠纷),观察其中对法源的选择、对法律的适用方式和最终判决对中方当事人经济利益造成的损害。或许这种细水长流、一点一滴的吸血型司法,才是领事裁判权所能带来的对列强最货真价实的利益,以及对中国最为无声又窒息的损害。列强甚至可能以其在外人杀华人这类重案中“秉公执法”的表象,来掩盖其在华洋商事纠纷中对中方利益的制度性、例行性掠夺。当然,这项工作需要跨学科的知识(如经济史知识),需要对大量中外文档案资料展开扎实的整理工作,甚至需要定量工具的协助,因此确实要耗费极大的人力资本。但我相信这一定是个极富意义的选题。
再如,本书已经深入探讨了清代法律职业群体这一议题,但在我看来该议题还值得以比较方式予以更全面、清晰的呈现。仅仅是证明清代中国“有”法律职业群体,可能还是不足以让受东方主义影响的人士们“服气”,毕竟他们会坚称清代即使“有”这类群体,但也是“不如”同时期西方的同类群体。因此,历史学家或许就有义务以中西比较的方式,对前近代和近代早期中国和西方(可以选取几个代表性国家,比如英、法、德)法律职业人员的整体规模、社会地位、职业能力、培养制度、选拔和晋升方式、对法律与社会发展的作用做出全面梳理。对法律东方主义在学术层面展开斗争,是一个艰巨而又长期的过程,比较法律史学也一定能在此过程中发挥价值。
结语
后殖民主义不是意识形态,相反它批判和解构一切意识形态。后殖民史学不只是可以用来“骂洋人”,更不是无关痛痒的方法论炫技或史学异端。后殖民史学的意义不仅在于批判历史上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而且有助于检讨被殖民地区学术与思想界长久以来顽固存在的自我殖民和自我东方主义现象。在当代中国学术界,我们仍然可以从后殖民史学中受益良多。正如本书所展示的,后殖民史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清算帝国时代的法律遗产,更敏锐地检讨象征性认知暴力导致的持续至今的、充满偏见的知识体系。只有在完成这些清算和检讨后,中国学术才能以更从容的角度快步向前,并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提供对全人类都有益的知识和理论贡献。我相信,《帝国时代的法律、知识与权力》一书,一定是这一知识事业中的重要参与者。









 蜀ICP备2022028980号-1
蜀ICP备2022028980号-1